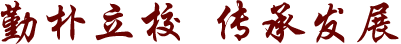革命烈士——殷夫
二十年代校友
殷夫从小就受到比较良好的家庭教育,大约在六、七岁时,入大徐村徐姓义塾,读了三四年“四书五经”与初小课程。1920年秋,进入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读书。当时,县立高小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较大,师生们经常在校内外宣传打倒列强,反对军阀。这使殷夫思想上受到了较深的启迪与教育。
1923年7月,殷夫在县立高小毕业,由徐培根接往上海,考入上海民立中学“新制初中一年级”。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民立中学师生积极参加“三罢”斗争,使殷夫受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五卅”运动后期,他一度回乡,在丹城和大徐家中认真阅读了许多革命书刊和理论著作,并参加过象山旅甬进步学生组成的革命文艺团体“新蚶社”的活动,还在该社举办的《新蚶》小报上发表过抨击封建礼教的新诗。同年9月,他仍回民立中学,读完初中二年级下学期及初中三年级的全部课程,于1926年夏初中毕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殷夫因一个广西籍同学“獐头小人”的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囚禁三月,险被枪决,后由大哥徐培根将他保释出来并予以“软禁”,并准备将其送进同济大学,企图利用德国人的力量来严加管束,并以优裕的生活条件诱使殷夫离开艰苦的革命斗争。
1927年9月,殷夫通过女友盛孰真借得上虞人徐文雄的高中毕业文凭,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共产党员王顺芳、陈元达等同学,并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校内外的秘密革命活动。他还办过油印文艺刊物《漠花》,在青年学生中鼓动革命情绪。后来,他又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多次在学生会上宣传革命道理,并跟反动学生进行过坚决地斗争。这时他由团转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一员。
1928年初,殷夫又在校外参加了共产党人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组成的“太阳社”,党的组织关系也编入该社,属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
1928年秋,殷夫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再次逮捕。当时他的大哥已在国外,由大嫂张芝荣转托徐培根在上海的熟人保释。获释后,他又回同济大学学习德文。党组织考虑到他和王顺芳、陈元达等人的安全,决定让他们暂时转移到象山。10月,殷夫先到丹城,在他二姐徐素云任校长的县立女子小学作代课教师。随后,王、陈也到象山(王改名汪涅夫),也在女子小学教书。他们三人都以“小学教员”作掩护,向师生宣传革命理论,并组织学生排练宣传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新剧目,进行街头演出,观者人山人海。他们以游览名胜为名,在丹城西寺、东乡珠山、爵溪沙滩、白墩码头等处秘密商讨革命问题。不久,女子小学放寒假,王顺芳、陈元达离开象山。殷夫则因大嫂张芝荣未给川资,不能同往。直到1929年3月,他才在二姐徐素云的资助下,离开凄清的象山西寺,回到战斗的黄浦江畔。回到上海后,经过一段“流浪”生活,他又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从此,他完全投入了地下革命斗争,从事青年运动工作,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活动,并宣告同反动阶级大哥的彻底决裂。为此,殷夫写下《别了,哥哥》这首诗,作为向一个阶级的告别词。诗人犹如暴风雨中的海燕,在工人运动的刀光剑影中,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他既是歌手,又是骁将。在战斗的间歇,他创作了一批被誉为红色鼓动诗的革命战歌。他的作品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用英雄的最强音,热烈歌颂了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
1929年6月,因向鲁迅主编的刊物投稿,而与鲁迅相识,自此得到了鲁迅的热情关怀和帮助,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殷夫开始翻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传记及作品。他根据德文版的《彼得菲诗集》中一首“格言”,翻译成被人们广泛传颂的四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激励了无数有志青年冲破封建牢笼献身于人民革命的解放事业。是年夏天,殷夫在参加上海丝厂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他没有让大哥大嫂来保释,以免再受他们的束缚。他被关了一段时间,受了几次毒打,终于获得了释放。不久,他就恢复了组织关系,担任了青年反帝大同盟,共产主义青年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殷夫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对于殷夫等同志的被难,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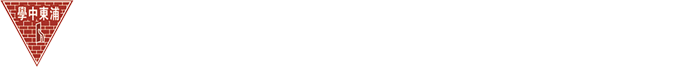



 沪公安网备31011502006273号
沪公安网备310115020062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