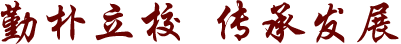一代法语宗师——何如
二十年代校友
何如(1909—1989年11月30日),广东梅县人。一代法语宗师,中国古典诗词外译的一代宗师,杰出的翻译家,法语教育家,毛泽东诗词的权威翻译家,被法国总统密特朗誉为“把毛主席的诗词译成法文的第一人”。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大学法语专业创始人,民盟盟员,1986年,法国总理希拉克委托法国驻华大使馆授予何如先生“法国教育部棕榈教育勋章”,以表彰他在宣传法国文化和中法文化交流中所作的贡献。
何如先生,1925年到上海浦东中学求学,后转学至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1927年赴法留学,为了打下扎实的基础,他先在巴黎拉加拿中学就读三年,然后考入巴黎大学就读六年,先后获法国文学、语言学、哲学三个硕士学位。1935年,当他还正在攻读大学时,他就以中国题材《贵妃怨》创作了一首法语长诗,在出版时轰动法国诗坛。从此人们对这位中国年青学生刮目相看,就连法国本世纪的、一向对他人评价很吝啬的伟大诗人保尔·瓦莱里也给予他高度的赞扬。这个“成功”应归于他的刻苦和严于律己的精神。
1936年7月回国,先后在重庆广播电台任法语编辑和兼职播音员、法国驻华顾问室译员,后又在国立艺专及陆军大学等单位执教法语。是时,他还被增补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先生曾先后在南京政治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教授法语。1949年后,他一直在南京大学执教法语,首聘二级教授,文革后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与此同时,他还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江苏省翻译协会顾问等职。
他擅长中法古典诗词的互译(中译法、法译中),而尤以中译法见长。他翻译了《木兰辞》、《十五贯》、《文心雕龙》、《杜甫诗选》、《屈原赋诗》、《毛主席诗词39首》、郭沫若的《女神》等中译法的古典诗词。不仅要忠于作者的原意,还要遵循法语古诗的各种规则(如音节、韵律等等),如没有渊博的知识,掌握大量的词汇量和高超的技巧,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著名比较文学家、翻译家沈大力先生如是说:“窃谓当代文学翻译家中,惟何如先生能有此引人进入化境的神来之笔”。
为了系统的介绍祖国文化,他还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和《中国古代史》等(中译法)著作。曾有一位法籍老华人笑问他:“先生何以厚爱古诗?”何答:“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其实,他也并非厚古薄今,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他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把《阿诗玛》、《王贵与李香香》、《红旗歌谣》等当代诗歌译成了法文诗歌,使外国朋友能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
何如在教学、工作之余全译或部分翻译了近十部中国文学名著、两部历史、一本寓言(法译中)以及数百篇政论文章;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的翻译,并担任毛选法语翻译的主审。他的译作,为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毛泽东选集》译著,几乎在所有的法语地区得到了传播:教科书的选用、杂志的刊头、广告的栏目、集会的朗诵……都引用过他那闪闪发光的译文。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访问南京大学演讲时,高度赞扬了何先生的学术水平;1986年,法国总理希拉克特委托法国驻华大使馆授予何先生《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此殊荣!
1956年夏天,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全过程的翻译;1963年刚译完《辛亥革命》,立即又参加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的若干重要评论员文章的翻译。为了保证《毛泽东选集》的翻译质量,他进驻北京,自告奋勇地担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及其他各卷很多篇章的定稿。每当毛主席诗词一首首发表,他就好象面对一块块无暇的美玉,废寝忘食地反复琢磨、推敲。他当之无愧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的评价和敬重。一封来自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让·玛丽·戴莱1979年10月写给译者的信,他说“……我不懂中文,过去因无法通过法文领略毛主席文学作品的瑰丽而一向深感遗憾,如今多亏您,我这种遗憾的心情已不复存在了,因为您那完美的写作手法、完美的韵律,使您翻译的诗篇清纯、含蓄,犹如用拉辛、维克多·雨果、兰博、瓦列里、阿拉贡、科克托的语言直接写成的(左列都是法国历代和当代的著名诗人—译者注)。同样也多亏您,我才更好理解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
何如老师常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教育和翻译事业了。何老自幼家境清寒,长期养成了他艰苦朴素的习惯,春秋总是那一套蓝布中装,冬天是蓝布棉服外加旧呢大衣,每件衣服不把它穿得旧烂绝不丢掉,几十年如一日。这倒并不是他添置不起,他认为只要内衣干净、外衣整洁,过得去就行了。他常在学生面前读他所译的两句法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 何如1.png 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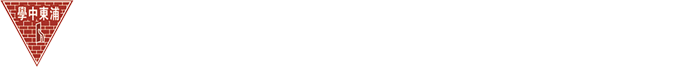



 沪公安网备31011502006273号
沪公安网备31011502006273号